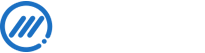加拿大作家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·门罗(Alice Munro) 于2024 年5月13 日去世,享年92 岁。诺奖颁奖词中称她写出了人心的异想,是当代短篇小说的大师。纪念一位作家最好的方式是阅读她的作品。今天我们推出门罗的《游离基》(Free Radical),让我们一起来阅读、讨论这篇小说。经典长存。愿门罗安息!
大家起先常打电话给妮塔,看她是不是太伤心、太寂寞,有没有食不下咽,或是喝过了头(她以前葡萄酒喝得多,很多人都忘了她现在必须滴酒不沾)。她叫他们别再打来,但语气既未强忍伤痛,也没故作开朗;既未魂不守舍,也没六神无主。她说她不需要别人帮忙买菜,她正忙着一一处理手边的事。医生开的药还够,要寄谢卡用的邮票也还有。
跟她比较亲的朋友大概也猜到了——实际的情况是,她根本没什么胃口,别人寄来的吊唁卡也全扔了。住得远一点的人,她连写信通知都省了,那些人自然不会寄吊唁卡来,像瑞奇住在美国亚历桑纳州的前妻,和那个住在新斯科细亚省、他已经不太往来的弟弟,她一律没联络。虽然这些人应该比她身边的人更能了解,她为何没举办告别式就直接下葬。
瑞奇当时曾打电话给她,说他要去村里的五金行一趟。那时是上午十点左右——他已经展开粉刷露台栏杆的工程,但先得把斑驳的外层刮掉才能上漆,旧刮刀偏巧坏了。
她没时间纳闷他为何不见人影。他在五金行门前的人行道招牌(上面写着割草机有打折)旁忽地弯下身来,就那样死了,连店门都没来得及踏进半步。他八十一岁,除了右耳有点听不见之外身体都好,而且上星期才去医生那边做过健康检查。妮塔在事后才看到一堆相关报导,很多猝死的人,在猝死前都刚做过健检。她说,机率高得有点吓人,你会觉得最好别去健检。
这些事情她本该跟她两个密友说的——维姬和卡洛,两人嘴巴都有点坏,两人都和她差不多岁数(她六十二)。不到这个年纪的人,会觉得聊这种事不妥当,也未必真能体会。起先她们还一副逼她吐露心事的样子,虽不是真的要她讲丧夫之痛的心路历程,但她真的很怕她们说不定哪天心血来潮就会发难。
她一开始安排瑞奇的后事,想当然,很多人都疏远了她,只剩下可靠的老朋友。她选了最便宜的棺木,而且要求立刻下葬,什么仪式都没有。殡葬业者说这样可能会违法,但她和瑞奇早就都问清楚了。他俩大概一年前就有了准备,那时医生诊断她的病情已经到了最末期。
大家没指望传统的告别式,但还是希望多少要有个场合,让大家歌颂生命的美好、放点他喜欢的音乐、大伙儿一起握着手,轮流说点关于瑞奇的故事,夸赞他多好多好,也免不了用他的小毛病和犯的小错开点玩笑。
所以瑞奇的后事很快就办妥了。事情刚发生时的不安、层层包围妮塔的温情,也逐渐淡去,虽然她知道有些人还是会说很担心她。维姬和卡洛倒没这么讲,只说假如她想现在一走了之,就是个自私的混帐。她们说会带伏特加来给她补一补。
去年春天她做的放疗还蛮有用,她的癌症目前正在缓解状态——天知道这是什么意思,反正不是“没了”,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关键是她的肝,只要她遵守小量进食,应该不会有大问题。问题也只有在她提醒朋友说她不能喝葡萄酒或伏特加时,朋友觉得扫兴而已。
瑞奇去年六月去世的。现在是仲夏。她早早起床、洗澡,手边有什么衣服就穿什么。不过她确实有穿衣服、有洗澡,还会刷牙梳头。她头发长回来不少,脸旁的毛发仍灰白,后脑勺则是黑色,一如既往。她会涂口红、描眉毛,尽管眉毛现在有点稀疏。她又看了一下自己的腰和臀(谁不爱丰臀纤腰呢),比照之前的模样,哪怕她心里明白,现在最适合形容她身体各部分的词,应该是“骨瘦如柴”吧。
她坐进她习惯坐的大扶手椅,身边是成堆的书和没拆封的杂志。她小心翼翼啜着马克杯里冲得很淡的花草茶,这现在成了咖啡的代替品。她一度以为自己少了咖啡就活不下去,结果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,其实是手里捧着暖呼呼的大马克杯的感觉。有杯在手,可以帮助她思考,不管她脑里想什么,无论几小时,或几天。
这是瑞奇的房子。他和贝蒂还是夫妻的时候买的。原本只是买来周末度假用,冬天就完全封起来。里面有两间小卧室、一个有单面斜屋顶的厨房,离村里半哩路而已。不过他很快便展开改建工程,不仅自己学了木工,还加盖了两面侧翼,一边是两间卧室和浴室,另一边是他的书房。原本的屋子就这样摇身一变,成为一个结合客厅、餐厅和厨房的开放式空间。贝蒂的兴致也被勾了起来,她一开始还说实在搞不懂他干嘛买间破烂屋,但一点一滴化腐朽为神奇的工程,总让她兴致勃勃,还给两人买了同花色的木匠围裙。她之前的几年一直忙于写食谱、出书,这些都告一段落之后,她需要投入新的工作。他们没有孩子。
贝蒂还跟别人说,她觉得当个木匠的好帮手,等于又在生命中找到了位置,她和瑞奇也因此变得比以前更亲,但同一时间,瑞奇却爱上了妮塔。瑞奇在大学里教中世纪文学,妮塔则是教务主任办公室的人。他俩头一次,是在一堆刨木片和锯断的木条里,日后变成了中央的大客厅和挑高天花板。妮塔把她的太阳眼镜忘在那边——她不是故意的,但从不丢三落四的贝蒂,自是不会相信。接下来当然是老套而磨人的一哭二闹三上吊,最后的结局是贝蒂去了加州,后又搬到亚历桑纳州;妮塔则在教务主任的建议下辞了工作,瑞奇因此无法升为文学院院长。他选择了提前退休,卖掉市区的房子。妮塔没有接收贝蒂的木匠围裙,却在一片混乱中开开心心看她的书,用电热炉做简单的晚餐,不时散长长的步,探索周遭的一切,带回长短不齐的虎百合和野胡萝卜花束,放进空油漆罐权充的花瓶。她和瑞奇安顿好之后,有时想起自己不知怎地一下子就成了那个年轻的新欢、得意的小三,活跃欢笑、蹦蹦跳跳的天真姑娘,不免多少有点汗颜。她个性其实一板一眼,是个笨手笨脚,在别人面前就不自在的女人(她早已不是女孩)。她能一一列出英国所有皇后(记得住国王很不错,但背得出皇后是本事),对三十年战争倒背如流,却不敢在别人面前跳舞,而且和贝蒂一样,怎么都不肯学着上梯子。
他们这屋子的一边有一排雪松,另一边则是铁轨的路堤。这里火车的流量并不大,现在一个月大概只有两班车。铁轨间长满了绿油油的杂草。她快迈入更年期时,有次曾跟瑞奇开玩笑,说两人可以到那边去——当然不是在枕木上,而是枕木旁狭窄的草堤上。于是他们真的爬下路堤,喜不自胜。
每天早晨她坐在自己惯常坐的位子时,总会仔细地把瑞奇不在的地方想过一遍。他不在小浴室,那里仍摆着他的刮胡用品,和一些治小病不管大病的处方药,他始终舍不得扔。他也不在卧室,她刚刚整理好了才走出房门。他也不在大浴室,他只有想泡澡的时候才会踏进这里。他也不在厨房,去年这里几乎成了他的地盘。他当然也不在刮漆刮了一半的露台,作势在窗口调皮地偷窥——他们刚同居的时候,她很可能曾在窗前假装要跳脱衣舞。
他不在书房。这里是最看得出他已不在人世的地方。起先她觉得有必要走到书房门前,打开门,就那么站着,扫视那成堆的纸、奄奄一息的电脑、散落四处的档案、向上或朝下摊开的书、书架上挤得满满的书。现在她已经练到只在脑中想像就够了。
就这阵子,她总会有一天踏进这书房。她一直觉得这是种侵犯,但她总得侵入亡夫已死的心灵。她之前从没有过这种念头。她总觉得瑞奇十足俐落能干,那么健壮、那么真实地存在,所以她始终相信(虽然很没道理)他会比她长寿。结果到了去年,这念头就一点都不荒谬了,但她觉得,他们俩心里都清楚这是必然的结局。
她打算先整理地窖。那确实是个地窖,不是地下室。泥土地上铺着木板做的步道,小小的顶窗布满肮脏的蜘蛛网。这里摆的东西,她没有一样用得着。只有瑞奇用到一半的油漆罐、存着备用且长度各异的木板、不知是有用还是准备要丢的各种工具。她以前只打开门下来过一次,看看是不是有灯没关,确定灯的开关都在,而且旁边都贴了贴纸,写着哪个开关控制哪盏灯。她上楼后,照例把厨房通往地窖的门闩上。瑞奇以前常笑她这个习惯,说地窖里是石墙,窗户又那么丁点大,问她觉得有什么东西能进来找麻烦。
她已经铺过床,把自己在厨房和浴室制造的小脏乱都整理好,但她完全没有来个大规模扫除的冲动。她这个人,连弄弯的回纹针、失去吸力的小磁铁都舍不得丢,怎么可能丢得掉她和瑞奇十五年前旅行时买的爱尔兰硬币碟?每样东西似乎都生出了自己特有的分量与亲疏。
卡洛或维姬每天打电话来,大多接近晚餐时分,想必她们以为她这个时候最受不了孤独。她说她很好,不久就会出关,她只是需要一段时间,就是想想事情、看点书。她吃得下、睡得着。
这些都算实话,但看书那部分除外。她置身自己的书堆中,却一本也没打开。她一直都爱看书——瑞奇正因如此,说她就是他要的女人,她可以静静地坐着看书,不吵他。但现在她连半页都看不下。
她也不是把书看完一次就不再看的那种人。《卡拉马助夫兄弟们》《弗洛斯河上的磨坊》《鸽之翼》《魔山》这几本书,她看了又看。她会拿着一本书,想读某个特别的段落吧——结果发现自己欲罢不能,又把整本书重新读过。她也看现代小说,而且总是选择小说。她不喜欢听人用“消遣”这词形容小说,搞不好还跟人认真争论过,说现实生活才是消遣。这观念太重要了,去吵它反嫌多余。
而现在,非常诡异的是,这一切都消失了。不单是因为瑞奇的死,也因为她满脑子都是自己的病。她想过,这改变是一时的,等她停了某种药,做完折腾人的疗程,那种魔力又会回来的。
有天早上,她先坐了一会儿,觉得很热,想说应该起来开风扇。她也可以为环保尽一份力,把前后门都打开,如果有风,就会透过纱窗吹进来。
她先把前门的锁打开。连半点晨曦都还没透进来,她就察觉门口一道黑影挡住了光。纱门外站着一个青年。纱门的钩子是扣上的。
“我不是存心要吓你。”他说。“我正在找有没有门铃什么的,还敲了一下门框,可是我猜你没听见。”
他的声音变了——有点嘶哑,音调高了几度,让她想起某个电视喜剧演员模仿乡下人嘟哝的模样。厨房天窗射下的光一照,她才发现他不怎么年轻。她方才开门时,只注意到他很瘦,因为背光,整张脸是黑的。但她现在看到的身子虽瘦却很憔悴,完全不是年轻男人的样子,朝她故作亲切地欠欠身。脸长而刚硬,淡蓝的眼相较之下很突出。表情带点玩笑,但藏着某种固执,好像他总能为所欲为。
“是这样的,我有糖尿病。”他说。“我不晓得你认不认识有糖尿病的人,不过糖尿病的人饿了就得吃东西,否则身体会出毛病。我来这里之前就该吃东西的,只是因为赶时间没来得及吃。你不介意我坐着吧?”
“我没什么东西。”她说。“有几个蛋,有时我会炒个蛋,浇上番茄酱吃。你想这样吃吗?我也可以烤点英式马芬面包。”
她在锅里打了两个蛋,把蛋黄弄散,用叉子搅动,又把马芬面包切对半,放进烤面包机。再从碗柜里拿了盘子,放在他面前,又到放餐具的抽屉里拿了刀叉。
“好漂亮的盘子。”他说,拿起盘子端详,仿佛上面映着他的脸。她要去看锅里的蛋时,听见盘子落地摔得粉碎的声音。
“噢,请原谅我。”他的声音又变了,变得尖锐,显然不怀好意。“看看了什么好事啊。”
他已弯身去捡地上的瓷盘碎片,拿起其中一片带尖角的。她把面包和蛋放在桌上的时候,他把那尖角沿着光溜溜的前臂轻轻往下划。细小的血珠浮现,起先是零星的几滴,接着便汇聚成一道血流。
“噢,不要紧的。”他说。“只是好玩。我知道怎么划着玩儿。要是我玩真的,就用不着番茄酱了,对吧?”
地上仍有些他没捡的碎片,她转身想去拿后门柜子里的扫帚来,他却闪电般一把抓住她的手臂。
“你坐下。我吃东西的时候,你就坐在这里。”他又举起流血的那只手臂给她看,然后用盘里的东西堆成一个鸡蛋满福堡,三两口吞下肚,而且咀嚼的时候还张着嘴。电热壶里的水烧开了。“你杯子里放的是茶包吗?”他问。
“别老说对不起好不好。如果你只有这玩意儿,那也只能这样啦。你根本就不相信我来这儿是为了检查保险丝,对吧?”
“你别太铁齿。”他啜口茶,扮了个鬼脸。“别因为你是老太太就议谨。外头什么样的人都有,什么都上。小婴儿啦、狗啦猫啦、老太太啦,还有老男人喔。这些人不讲究的,可我讲究。我对不正常的方式没兴趣,我只想跟我喜欢的好女人做,她也要喜欢我才行。所以你放心吧。”
“刚刚有那么一下子,原以为你骗我你有先生。反正就算你骗我也没用。女人不是一个人住,我一看就知道。只要一进屋我就知道。女人一开门我就知道。我就是有这种直觉。嗯,这车状况还好吗?你知道他最后一次开是什么时候?”
“那好。”他把椅子往后推,压到地上的某片盘子碎片。他起身,有点吃惊地摇摇头,又坐回去。
“我累死了,得坐一会儿。我以为吃了东西以后会好一点儿。刚刚说我有糖尿病,是骗你的。”
“等我说拿你再去拿。我沿着铁轨走,一班火车也没瞧见。我一路走到这边来,一班火车也没有。”
“噢,那好。我下了水沟,沿着它走过几个丑不拉几的小镇,然后天亮了,我人也还好好的,只是已经到了水沟和马路的交界,我就赶紧溜开。然后我看到这边,有房子,有车,我就跟自己说,就这家。我是可以开我老爸的车,不过我这人还有点头脑。”
之后,打从他进屋以来,她头一次想起自己的癌症。想到这病反而救了她,让她免于凶险。
那是一张三人合照,在客厅里拍的,背景是拉上的窗帘,上面有花朵图样。一个大约六十几岁、不算太老的老男人,和一个差不多岁数的女人,一起坐在沙发上。还有个块头很大的年轻女子,坐在轮椅上,紧靠沙发一端,占了沙发前方一小块空间。老男人也是大个子,满头白发,眯着眼,嘴巴微张,仿佛一口气上不来的样子,不过看得出他努力挤出笑容。老妇人个头小很多,染了黑头发,涂了口红,穿着过去所谓的农妇装,手腕和颈际都有小小的红蝴蝶结。她的笑容就笃定得多,甚至笑得有点过头,嘴唇拉得宽宽的,正好盖住一口烂牙。
不过照片里最醒目的,是那个年轻女子。她穿了件鲜艳的夏威夷姆姆装,样子实在不像个平常人,而且暴丑。黑发沿着额头卷成一排小卷,双颊垂落颈间。虽然一身横肉,她倒一副很满足的神情,带点狡黯。
“她生下来就有问题,医生救不了她,也没人救得了她。她食量超恐怖,而且打从我有记忆以来,我和她就是不对头。她比我大五岁,生来就是存心整我的。拿到东西就朝我扔,把我打趴就算了,还想用轮椅来压我。对不起,我说脏话。”
“哼。他们就当没看见。他们去教会,牧师说她是上帝的恩赐。他们带她上教会,她去嚎得跟后院里猫一样。他们居然还说,噢,她想奏出音乐,噢,上帝祝福她。对不起,我又说脏话了。”
“所以我从不喜欢待在家,就自己出去讨生活。那也没关系,我跟自己说,我才不要待在这里忍受这堆鸟事。我有自己的生活。我找了工作,而且几乎都找得到事做。我才不会一坐着,只知道拿政府的钱喝酒。噢,我是说臀部啦。我从没跟我老爸伸手要钱。九十度的大热天里,我照样起床给屋顶上柏油。我在又臭又旧的餐厅擦过地板,也在专门骗钱的烂修车厂当过黑手。有活我就干。可是有时候我又不吃他们那套,所以都做不久。就是一般人拿来对付我这种人的那一套,我受不了。我家是正正当当的家庭。我爸做工做了一辈子,做到病了做不动为止,他是开公车的。我生来不是要忍受这些鸟事的。好——先不讲这个。我老爸老妈常跟我说,房子是你的。房子贷款都付清了,状况也好,是给你的。他们话是这么说喔。我们晓得你小时候吃了不少苦,要不是这样,你大可以好好上学,所以我们想尽力补偿你一点。所以不久前,我打电话给我爸,他说,当然喽,你知道我们约好了嘛。我说约好什么?他说,就是约好,你签字同意照顾你姐姐一辈子。你要答应这房子也是她家,才能分一份,他说。”
“我老天啊,这是哪门子说法?我从来没听过这种约定好吗?我一直都以为我们讲好,等他们死了,她会去安养院。结果现在房子不是我的。”
“所以我跟我老头说,我的想法不是这样,他说,所有文件都弄好了,只等你签名,要是你不想签也没关系。你蕾妮阿姨会盯着,等我们走了,她会看你有没有遵守约定。”
“总之一听他说你蕾妮阿姨会盯着你,我突然就改了主意。我说,那好吧,我想就这么办吧,也算公道。就这样吧。好,我这个星期天过去和你们吃晚饭,好吗?”
“当然好,他说。很高兴你变得这么懂事。你老是动不动就发火,他说,你都长这么大了,应该懂点道理。”
所以星期天我就去了。我妈已经烤了鸡,我一进屋子就闻到那个香味。然后我就闻到玛德琳那个噁心的老味道,我不晓得那是什么味道,可是就算我妈每天帮她洗澡,那味道还是洗不掉。不过我对他们都很好。我说,机会难得,我应该帮他们拍张照。我说我买了这个超棒的新相机,照片一下子就洗出来,马上可以看喔。拍好就能看,怎么样,很赞吧?我安排他们都坐在客厅,就像你看的那张照片那样。我妈说能不能快一点,我还要回厨房干活。我说很快就好,然后我就拍了。她说,来吧,看看拍得怎样。
我说,等等,再等一下,一分钟就好。他们等照片的时候,我拿出我那把很棒的小枪,砰砰砰,把他们全干掉了。然后我又拍了一张照片,再去厨房吃了点鸡肉,看都没看他们一眼。我原本以为蕾妮阿姨也会在,可是我妈说她去忙教会的事。如果她在,我也会轻而易举干掉她。你看,这是之前,这是之后。
老男人的头往旁倒,老妇人的头往后仰。表情已被枪轰得稀烂。他姐姐往前仆,所以看不到脸,只见她被花朵图样洋装包住的膝,黑发编成精美而过时的发型。
“我是可以坐在那儿自爽一整个礼拜,感觉超轻松的,不过我没过夜就走了。我确定自己把东西全清干净、把鸡吃光,就想说该走了。我原本想等蕾妮阿姨进来的,可是之前的那种情绪已经没了,真的要做掉她,我还得培养那种情绪,但我已经没感觉了。而且,我吃得好撑,都是那只超大的烤鸡害的。我得吃掉它,没办法带走,因为我怕狗会闻到味道,如果我照计划走后巷出去,怕会打草惊蛇。我想吃了这一大只鸡,应该够我撑一个礼拜吧,结果你看,我找上你的时候,饿得跟什么一样。”
如果他喝了酒,是否会稍稍放松戒备?会不会比较好讲话?还是反而会变得更凶更狠?她要怎么看出来?结果她不必走出厨房就找到了酒。以前她和瑞奇习惯每天喝一点儿红酒,据说对心脏有益,或是可以杀掉对心脏有害的什么东西。她这会儿心里害怕又六神无主,根本想不起那东西叫什么。
因为她吓坏了。这也难怪。她罹癌,对眼下这种状况一点帮助也没有,完全没有。她活不过一年,丝毫动摇不了她现在就可能一命呜呼的事实。
他又说了:“啊,这是好酒,不是用转的那种瓶盖。你有软木塞开瓶器吗?”她走向抽屉,但他随即起身把她推到一边,还好力道不重。
“别别别,我来就好。你离抽屉远一点。噢,天啊,这里还真有不少好东西咧。”他把刀子全放在自己位子上,她够不到的地方。然后用开瓶器开了酒。她察觉开瓶器在他手里也可以是种利器,但她自忖能用上它的机率并不高。
“我只是要拿玻璃杯。”她说,但他回绝了。不要玻璃的,他说,有没有塑胶的?
“我也只要一点点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“我还得开车。”可是他还是把酒一直加到杯口。“我可不希望警察把头伸进车来,看我喝酒没。”,
“是红酒里面的东西。红酒会破坏它,因为它有害;还是会培养它,因为它有益?我记不得了。”
她啜了一小口酒,倒没有她想的不舒服。他也喝了,但人仍站着。她说:“你坐下的时候,小心那些刀子。”
“当然没。你以为我是什么杀人犯?是啦,我是把他们干掉了,但我不是杀人犯。”
“我不知道蔬菜的毒是不是真的,反正没人想得到要去查。这女的小时候得了风湿热,后来就一直拖着这病,什么运动都没法做,别的事也做不了,老是得坐着休息。说她快死了也不意外。”
“我先生爱上她,而且想甩了我娶她。他跟我说了。我为他真是做牛做马,我和他一起改建这间房子,他是我的一切。我们俩没有小孩,因为他不想要。我学了木工,而且我明明很怕上梯子,为了他我还是上去了。他是我的命啊。结果呢?他一脚把我踢开,要去找教务主任办公室那只没用的病猫。我们努力打造的一切,结果只是方便他去找她。这公平吗?”
“我不用弄,后院就有。你看,那里有一片大黄,几年前就种了。大黄叶子的叶脉里就有毒,正好合用。不是大黄的茎,茎是我们平常吃的,那没问题。不过你看大黄的大叶片,里面细细红红的叶脉就是有毒的地方。这件事我早就知道,可是我得老实说,我还真不知道那毒怎样才会发作,所以我想说那就实验一下。这中间有几件事我还真走运。首先,我先生出差去明尼那波里斯开会,当然他也可能带她一起去,不过那时是暑假,她在办公室资历最浅,必须留守,休不了假。还有我也得想到,她好像不是一直都一个人,说不定会有人在她旁边走来走去。此外,她也可能对我起疑心。我得假定她不晓得我知情,还是把我当朋友。我家办派对的时候她来过,我们处得还不错。我先生做什么都拖拖拉拉,所以我得假设,他跟我承认他在外面有人,好看我的反应,却还没跟她说他已经告诉我了。也许你会说,干嘛把她做了?说不定他两边都在考虑?
“不会。他跟她应该不会断。就算他放弃她,我们的生活也被她毁了。她毁了我,所以我也要毁了她。”
“我烤了两个大黄塔,一个里面放了毒叶脉,一个没有。当然我已经把没毒的做好记号。我开车去大学,买了两杯咖啡,走到她办公室。那里只有她一个人。我跟她说,我去城里办点事情,路过大学的时候,看到我先生提过的一间小面包店,他说那边的咖啡和点心都很不错,我就进去买了两个塔和两杯咖啡。我想说大家都放假去了,她一个人当班应该很孤单吧,我先生去出差,所以我们俩是同病相怜嘛。她人很好,看我这样做,她很感动,说她一个人无聊得很,学生餐厅放假又不开,所以咖啡要老远跑去理学院大楼买,但那边的咖啡又加了盐酸。哈哈。所以我们俩就喝起下午茶了。”
“可对她有用啊。我得赌它效果够快,得在她发现不对劲、跑去洗胃之前就发作,可是又不能快得让她想到跟我有关。我得尽快脱身,所以我就走了。大楼里面没什么人,就我所知,我进来出去,都没人看到。当然,我知道后面有小路可以出去。”
“我也非这样做不可。我保住了我的婚姻。他后来也明白,和她在一起不会有好下场。她最后肯定会病倒,他会落得要照顾她。她就是这种人,对他只是负担。他看到了。”
“当然没放啦。我也不想。你哪会三不五时就做这种事。我也不是真的懂下毒,只是碰巧知道这一点而已。”
那一刻或许就会来临。她一旦把钥匙给他,那一刻或许就会来临。如果她告诉他,她得了癌症,就快死了,能救她一命吗?真够蠢的,讲了也一点用都没有。就算她日后因癌而死,今天这件事照样会发生。
“我今天跟你说的事,我从没跟别人说过。”她说。“你是唯一一个听过的人。”
“还没有人知道呢。”他回道。她心想,感谢上帝,他满上道的,他懂的吧。他真懂吗?
“你给我闭嘴。闭嘴!否则我就叫你永远闭嘴。”他把拳头伸进蓝茶壶里,却伸不进去。“干,干,干。”他大吼,把茶壶倒过来,往梳理台上砸。结果除了车钥匙之外,家的钥匙、一堆硬币,外加一卷加拿大轮胎公司印的折价券,统统掉到地上,蓝茶壶也碎了一地。
她一时没想到这句话的含意,等她会意过来,觉得房间都颤抖了。“谢谢你。”她说,但嘴巴太干,她不知发出声音没有。不过想必她有,因为他回道:“先别谢我。”
“我记性很好的。”他说。“很久以前的事情,我都记得很清楚。你别把那个不认识的人说得像我,你总不希望他们去墓园把尸体挖出来吧。你只要记住,要是你漏一个字,我也会漏一个字。”
人走了。门关上了。她还是动也没动。她想锁门,却动不了。她听见引擎发动又熄火的声音。发生什么事?他这人很暴躁,发动的程序很可能完全不对。接着又是发动的声音,发动车子转出去的声音。轮胎摩擦碎石路面的声音。她颤抖着走到电话旁,发现他说的是实话,电话线被剪了。
电话旁边有个书柜(他们家书柜很多),里面放的大多是很旧的书,好几年没打开了。有《骄傲之塔》。有亚伯特•史毕尔的书。瑞奇的书。
《常见蔬果大惊奇:丰盛优雅的餐点与新鲜的惊喜》。调制、测试、创作的人,都是——贝蒂•昂德希尔。
她和瑞奇刚把厨房盖好的那阵子,她曾试过模仿贝蒂做菜的风味,不过终究是白忙一场,而且没多久就放弃了。一来瑞奇无意重温在厨房费事张罗的苦头,二来她自己也没耐性花那么多时间,又切又剁又要小火慢熬。不过她确实学到不少让她意外的知识,比方说,某些大致无害的常见植物,有些部分居然有毒。
瑞奇。瑞奇。她现在终于晓得真正思念他的滋味。就像天空中的空气全被抽走一样。她应该走到村里。行政中心后面有间警察局。
一阵敲门声把她吵醒。门仍然没上锁。门口是个警察,不是村里那个,而是该省的交警。他问她是否知道她车的下落。
“我得跟你说,出了 一场很严重的车祸,就在瓦伦史坦这边,只有一辆车的车祸。司机连人带车滚进涵洞,整个撞烂了。不过还有戏咧。这个人因为三尸命案被通缉呢。 我们听到的最新消息是这样。在米契尔斯顿的谋杀案。你没碰到他,真是走运。”
之后,警察好心地训了她一顿。钥匙留在车里,又是独居女性。现在这年头你永远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。
爱丽丝·门罗(Alice Munro), 加拿大女作家,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,三次获得加拿大总督奖,于2009年获得布克国际奖。2013年,以“当代短篇小说大师”的成就,成为第一位加拿大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,也是第13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。2024年5月13日,她在加拿大安大略家中去世,享年92岁。
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,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,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,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。公海赌赌船官网
本文由:公海赌赌船汽车保养服务网站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