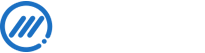正是圣诞节前,星巴克的装饰充满了圣诞的气息,我坐在这个宽敞的咖啡厅的角落,第一次不戴眼镜看清了挂牌上“星冰乐”几个字,我兴致勃勃点了一杯季节限定口味的咖啡,味道像是在咖啡里溶了一个苹果派,我很喜欢。
好兴致没有持续太久,直到到手机上显示母亲的来电。或许她只是想问我在忙什么,我要不要就在直接告诉她我做了近视眼手术,也没什么不好,父母两人早晚也会知道,只是不知道他们俩人是否还会像之前那般生气,承受单方面浓烈的情绪宣泄,像上次那样让我生气得按掉视频,还是第一次。
深呼吸,“我来做近视眼手术。”看,说出来也没多难,我就应该永远投直球,一颗球咻咻得划破空气,我只管奋力的投出就好。
是啊,本来还有些纠结犹豫的,偏偏是和父母争吵了一番,拉锯的平衡被打破,这近视眼手术我倒是非做不可了。
我绝不是叛逆期上头了,就是要逆这父母的意思行事。难不成我三十岁才拥有了迟来的叛逆,那种从不曾在我的青春期出现的东西?
青春期里我也是那种太乖的小孩子,有一张你能想象到的贫乏的中学生的脸,没有刘海,壮实的马尾辫,一身黑蓝色的运动装校服,脸上架着一副眼镜。700度的近视是不能没有眼镜的,它牢牢在我的鼻梁上留下两个深痕。
我不知道体育课跑800米我总是跑不动是否和眼镜有关,汗水让我的脸颊滑腻腻的,眼镜就会顺着我的塌鼻梁向下滑。“摆臂,把手臂摆动起来。”体育老师喊着,我的手臂要么在胸前按住没有运动内衣保护的前胸,要么抬起来推一推眼镜。
带上眼镜的时候是转学后的初二,这样爸妈总不至于为了座位位置去找老师谈谈。我座位的斜对角坐着一个长相甜美的女生,有时候看到她把眼睛松松地架在鼻尖上,透过眼镜的上缘眨着大眼睛和别人说话。我眼见着我暗恋的男孩,眼睛和心都飞在了她身上。
“她就不能好好戴眼镜么。”我跟朋友抱怨道,我对着镜子自己试着把眼镜架在鼻尖上,不行,一转头就会掉,而且我什么也看不清,都看不清喜欢的男孩子在哪,怎么送秋波,而且,我知道,他不喜欢我。
纵然如此,我还是很愿意戴眼镜的,好歹亲朋好友愿意用“显得文静”,“有书卷气”来形容我,好过“结实”“壮实”这种不属于青春期伤痛文学的形容词。
我拥有一种典型的青春期乖乖女的路径,伴随着青春期肥胖,我带上粗黑框眼镜,好不容易等到婴儿肥渐渐褪去,青春痘又爬满了额头,情不自禁剪了厚厚刘海去遮挡,痘痘就拉锯战一般的占领了我的全脸。
我那时就觉得,这世界是不会给丑女孩不乖的机会。青春期的女孩分两种,有一些女孩子皮肤细腻不会发胖,身材轻盈,萦绕着一种洛丽塔书中描述的那种纤细和风情,而另一种我这样的女孩子,雌性激素如同飓风过境,在敏感的少女心思上压着我的体重和好食欲,面对同龄的未发育的男孩子,我也能说:“别惹我,我一个打你们十个”。
眼镜就好像是我能守住所谓气质中的最后一环,还能修饰我的脸型,遮住塌鼻梁,不管换多少次眼镜,我都很偏爱小巧的镜片和纤细的镜框,尽管我要被不断提醒,这种设计不适合我的度数,会让700度的厚度无处躲藏。
我也不是没带过隐形眼镜,克服了手指头伸进眼睛拿捏的恐惧后,无法克服的是每次摘下隐形眼镜戴上框架镜时的头晕目眩,因为我的度数不低,镜片和瞳孔之间的距离变化,都像蝴蝶在我的脑海里煽动了一次飓风。我的学习和工作还涉及各种化学试剂,尽管架着护目镜,但万一有一滴试剂角度刁钻的飞溅入眼,隐形眼镜引发的后果我将无法承担。
“你家姑娘没做个近视眼手术吗?”邻居问到,“好多朋友家孩子都做了,就不用带眼镜了。”
“别去。”这就是我爸爸能给的嘱托。“我同事的老婆是眼科医生,看到不知道多少手术失败的人。”我心里却也不禁嘀咕,只有手术不成功的人才会去看医生啊,这是一种不幸者偏差吧。
我的父母也都戴眼镜,但我不觉得他们可以被称为近视眼患者。我爸爸在他二十出头的年纪,陷入了我和一样的“文质彬彬偏爱症”,他自述是为了“遮丑”,堂而皇之的带了眼镜这么多年,现在刷抖音小视频反而还要把眼镜架在额头上。我妈妈是在四十多岁的年纪,用眼镜来遮住膨出的眼袋,明明不近视,偏又觉得只带镜框不得体,硬是带上可有可无的一百度眼镜。
虽然眼镜可以修饰我的脸型,遮住我的塌鼻梁,但我一直忽视了,我的眼睛还是很好看的,这是我脸上最自信的部位。
我要不要做近视手术,我还是偶尔问问自己。二十出头时我跟自己说,还不行,我的度数不稳定,二十四五岁时候,连着几次配眼镜度数都没有变化,但手术费用对穷学生的我而言也过于高昂。二十八九岁,度数也稳定了,闲钱也有些,再三犹豫,而这一犹豫就是疫情三年。
小红书就是能读心,当我搜索起近视眼,与之相关的手术,广告,个人经验,好的坏的,纷至沓来。“手术效果特别好,早知道这样我早就做了”,这是个成功案例,“避雷贴,xx医院承诺主任医师做手术,最后不是他本人。”这有医疗纠纷。“我家人二十年前做的,现在有xxx的问题”,这个手术后续问题。
我不禁和其他网友讨论,跟手术机构的客服闲聊了起来,但所有人给的建议都是去医院先检查一下。也好,如果医生说我的眼睛有其他并发症的可能,或者完全不适合近视眼手术,那我也不必每次纠结犹豫。如果有了医生的支持,告知我爸妈我也会硬气一些,想到这些,仿佛又听到我爸妈在我耳边说了无数次的“别做”,“万一失败呢”。
“你好,我是第一次来做检查的,近视眼手术的检查。”填表,挂号,缴费,周六这天人没有很多,候诊区多是像我一样单独一人来咨询检查的,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年轻的妈妈,在其他门诊检查过小朋友视力,顺便咨询自己眼睛。还有一群高中生,估计是要是在高考前半年先把手术做完。做完手术闭目养神的,他们头上带着蓝色一次性手术帽上面贴着名字,看穿着打扮,有大学生,被男女朋友或者舍友陪伴而来,有父母就在身边的年轻人,也有夫妻陪伴而来的中年人,做完手术人们脸色平静,我会不会也是下一个他们呢?
“下一个,洋一。”医生叫我了,他面前放着我过去一小时做的各种检查结果,我像一颗要被验明真伪的玉石,被各种机器扫视,打光,吹气。我的检查结果五彩斑斓,像是一个描绘了我眼睛山川地貌的地图。
医生快速翻看了我的检查报告,在一些数值上面圈圈画画,“目前的手术的术式你有了解吗?”,“我了解。”我在决定检查前,就已经在网上看过科普视频,半飞秒,全飞秒和icl晶体植入,我都已经了解了大概。半飞秒是在角膜上切个270度圆弧,掀开角膜激光切削,再覆盖上角膜;全飞秒是切开一个小口,拿出激光切去的角膜即可;晶体植入就是切开一个小口,填入合适你度数的小眼镜。
“以你的眼睛条件,这些手术术式你可以自己选,你的眼睛都可以做。”真是个好消息,看这位主任医师松弛的表情,感觉我会是他众多经手的手术中,平平常常的那一个。做什么手术完全可以按照我的经济条件和心理承受来选择,什么时候想做,我都可以后续再安排,回程的路上,我整个人都雀跃了起来。
我要是不戴眼镜了,会方便很多吧,下雨天骑车眼镜上不会水雾迷蒙,冬天走入食堂,不会看不清菜品,擦拭多了的镜片也总会布满划痕。要是不带眼镜,这些问题终于不再是问题了。
“我今天去上海检查了一下眼睛,看看能不能做手术。”我有点兴奋地跟妈妈视频着。
脚步声,是我父亲走来,“你女儿要做近视眼手术,你说说。”我看到父母俩人交换了一个不满的眼神,我隐隐有了不详的预感。随即,疾风骤雨似的,坍塌的情绪像滑坡一般像我奔涌而来。似曾相识的无力感,笨拙的舌头,逐渐接管了我的身体。
“你怎么想做手术呢,你这也已经毕业了工作了,婚都结了,用不着做手术了啊!”
我沸腾的血液不断冲向我的脑袋,我已经区分不清他们俩人谁说了什么,脑海中反复就剩一句话,“我就不该告诉你们。”我是带着雀跃的心情来分享的,来告知的,不是来征求同意,我愤怒地按掉视频,把手机丢得远远的。
为什么呢,你们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,为什么我工作了结婚了,再做近视眼手术是为了臭美呢,臭美是什么词啊,我怎么就不能为了美,更何况我只是为了更便利的生活啊。你们带着装饰一般的眼镜,线度近视的生活是什么吗,我掉了东西,只能蹲着用手到处摸索,我摘掉眼镜就像个瞎子一样活着,怎么能对我的不便视而不见呢!
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问我,到底我能选什么术式?那我会告诉你,半飞秒切口大,全飞秒和icl的切口小,小到大部分的人不需要格外请假,过一个周末可以继续上班上学。
为什么不问问我做了什么样的检查,我会告诉你们,我角膜厚度中等,在手术安全的范围内,我的眼睛不干,术后干眼的概率不大,但我很有可能会眩光,但高度近视的我不做手术也眩光。
为什么不能再仔细回想一下,我在过去的四五年间提过几次我有做手术的想法,或许时机还不成熟,但我一直说我会问医生的意见,我没放弃。
我的手机一直不断震动,一条条60秒的语音不断传来,肯定是我按掉视频,燃起了我爸的怒火,他愤怒的火舌点燃各处,寸草不生。
他们怎么能这么愤怒呢,他们怎么能比我还愤怒呢,我为什么近视到700度他们不清楚吗,就算是我坐姿不好,握笔不对,爱看闲书,重点是这些吗?
根本不是,让我颇有怨气的真相是,我从告知父母我看不清黑板到配第一副眼镜中间居然间隔了五年!
在我做检查的医院一楼,是儿童视力矫正区,好多小朋友在爸妈陪同下尽早保护视力,小孩在小熊样子的椅子上爬上爬下。不禁让我回想起我第一次去医院配眼镜,滴了散瞳的药水,坐在那台电子测视力的仪器前,第一次看到那个图片,一条草坪上长长的甬道,尽头是一座红顶房子。
医生很错愕地问我妈妈,“第一次配眼镜,这都快六百度了,怎么才来配呢?”在我妈妈惊讶的表情中,我只能说:“我早就告诉过你。”早些时候的告知,换来的是我爸爸的“土法炼钢”,用一些道听途说或者一知半解的法子来“缓解”近视。他叫我练习“远眺”,现在回想如果在室外远眺或许是有帮助的,室外的光线有助于视力的调节,但在室内练习远眺,只是螳臂当车。
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练习“远眺”,“看运动的乒乓球”,都不能缓解我爸爸口中的“假性近视”,这才被逼正视这个问题,但无知和忽视,让简单的问题耽误五年,我的心里都还像有颗石子,偶尔硬生生地硌疼我一下。
我知道我的父母是那种“good enough parents”,但是对于视力保护他们是没有足够的认知来支撑的。这世界上,过时的观点往往比过时的技术更长久于世。
我是一个自食其力的成年人,我有经济能力和认知为自己做决定,我要把自己再“养育”一遍。
为这个做手术的周六,我已经做了快一周的准备。之前护士小姐姐给我开了瓶眼药水,用来避免眼睛发炎滋生细菌,术前三天早晚一滴,我还领了一张圆卡片,卡片正中有个绿色的圆点,每天睡前要求我每只眼睛盯着这个圆点练习固视,固定我的视线,因为作为病人在这个手术中唯一要做到的,就是盯住绿色激光点不动。
手术这天在我老公的陪伴下准时到达医院,我把手机手表耳饰都摘下,让他等待我胜利的好消息。
我穿上鞋套,手术大门在我身后缓缓关上,护士走来利索挽起我的头发塞在手术帽中,给我穿上了宽大的绿色罩衣。
“洋一,做什么手术。”一个助理医生问到。“全飞秒” “哪只眼睛?”我犹疑的回答:“两只眼睛”。我身边还有几位因为青光眼和白内障要做手术的爷爷奶奶,看来这个问题一定有存在的意义。
医生拿生理盐水清洗了我的眼周,我用手托着一个有弧度的托盘在脸边承接,刚开始没有贴紧,生理盐水扑簌簌地顺着衣领溜进我的衬衫里,冰冰凉。医生牵着我的手,引我坐在手术门口,我和另外一个女生看来是这个时间段唯二的两位病人。
等待的时候,看不见的时候,耳朵好像灵敏了起来,走廊另一边是另一位在刷手的医生,跟上年纪的护士愉快的讨论调休的事宜,滑门划开又关上,医生走进又走开。
“洋一,进来吧,在床上躺好。”医生滴好麻药,再次跟我确认姓名和手术术式,“记得盯着绿色光点不要移动。”扩眼器被放在了眼中,它可以避免我眨眼睛。我听到助理医生念了六位数的密码,后来我才知道手术最贵的恰恰是这专利需要的六位密码,因为手术是双眼,所以要付两次专利费。
机器发出女性英语提示音,表示准备完毕,“放松不要紧张。”我看到绿色的光点了,很亮,盯着不要动,视野里逐渐出现一系列逆时针的小点,逐渐从外围到中心,视野逐渐变得雾蒙蒙的,我看不清绿色的光点了。“这时候看不见光点很正常,一切顺利,不要动。”医生平静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,“还有10秒”。随着轻微的“啵”的一声,手术结束,“啵”的一声就是最后切开的小小开口。
这也太酷了,熟悉了这个流程第二只眼睛做的时候,我还能分心去赞叹手术的精巧,激光手术居然可以控制的如此精细,如此自动化的精细操作让我心悦诚服。
再次听到“啵”的一声,两只眼睛都结束了,接下来医生拿出一根精细的刮刀,从开口处伸进眼中,将激光切下的角膜拿出,医生的手法稳定且娴熟,病人本人可以全程清醒盯着医生的操作,这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体验吧。
我的视野变得明亮起来,但依然是雾蒙蒙的,像新娘子脸上的白色头纱,医生很高兴地说:“真好,手术非常顺利。”虽然还看不清他的表情,我的心情也被他的语气带着舒坦了起来。
在被护士观察的半小时里,我又被滴了数次眼药水,我眉飞色舞跟老公讲这个手术有多酷,可惜他不近视,他体验不了有多酷。
近视眼手术做完的第二天,早起定时按照医生嘱托点好了眼药水,这时视野里已经清晰了很多,只是依然还有朦胧的感觉。之后去医院复查,视线随着护士小姐姐的手指,终于看到了视力表最后的四五行。
“恢复还不错,一只眼睛视力已经到了1.0,另一只恢复慢一些,现在是0.8。”医生用裂隙灯仔细看了昨天手术的切口,“角膜也恢复透明,目前总体手术没什么问题,记得定期来复查。”
“那你的手术怎么样?”我听到电话那边妈妈问到,“很顺利,目前恢复的不错。公海赌赌船官方网站”妈妈在那头沉吟了一会,“后来我跟你爸也问了一些同事朋友,才发现好多人都做过激光手术了,都说好像还不错。”
是吧,对于我的父母来说,多少数据和案例都不如身边有认识的人现身说法。我先斩后奏,我感觉一阵舒服畅快。这种畅快绝非是少年时期反抗权威带来的刺激,而是我足可以证明我能好好生活带来的畅快。
之前争吵时,我不断争道:“我都三十多岁了,我自己能做决定。”“你多少岁,你都是我孩子,我五十多岁难道不是你爷爷的孩子吗?”是的,我是我父母的孩子,但不再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幼儿,爸爸无处宣泄的保护欲,想把我按在少儿的时间刻度上,但我只会被时间毫不留情带入中年,在刻度上留下一个少女的残影。
或者,是因为我依然还没有自己的孩子,我的父母没有更脆弱的对比,总觉得我依然是一个会冲动莽撞奔跑在世界上的无知少女,尽管我已经念完书参加工作并且找到人生伴侣,他们依然愿意为了我不管不顾的对抗整个世界。
我的父母很爱我,我知道,但没人能对待三十多的女人如同对待十三岁的少女,我理解他们的恐惧,我就像一位开着名为人生的汽车,纵使我过去十多年零违章,只要我驶向他们未曾途径的新的路段,无数个“万一”就会涌入心头,甚至让他们试图再次握住我的方向盘,我能做的只能是不断证明,这是我的人生,我走在我要去的路上,方向盘只能卧在我的手里。
我后来知道,我和父母大吵一架第二天,我老公给我父母留了言,很长的一段,其中他说“她是我认识人中非常聪明的女人,我相信她能好决定,并且承担后果,我永远站在她身后支持她,我觉得你们也该这样。”这或许也是我父母后面软化的一个原因,他站在我和我父母中间,帮我告诉他们,我真的不是一个小孩子了。
激光手术已做完半年,近期去复查我的视力已经到了1.2,医生都说,就手术而言几乎是完美的,不过眼睛的保护是后面一辈子的事,而且没人知道是不是会有后遗症,但就像没人知道意外明天那个先到来,我只能选择那个大概率的人生。
复查的时候在护士站签字,那一页纸上来复查的人出乎意料多是三十多岁的人,或许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,不再为了求偶求学和求职,纯粹只是为了自己,为了更有质量的下半辈子,为了再次养育自己,不仅仅二十多岁的年纪值得好好去过,每一个年纪,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去过。
一个能触动我的瞬间,都逐渐能长成一个故事。再次来到短故事,是在上旬一个疲惫的工作日,被工作摇摆到失衡的内心,需要文字重新稳住。但与此同时生活中的琐事接踵而至,在最后的dead line完成写作,感谢珍妮不断把我拉回写作的状态中,有时丰沛的时刻到来,无论如何都想写下文字来。
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,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,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,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。
本文由:公海赌赌船汽车保养服务网站提供